在过去,在老家,每逢天黑的时候,能照亮世界的便是煤油灯了。因此,我对于煤油灯的记忆是相当深刻的,也是很清晰的。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温馨与甜蜜。
小时候,父亲是小学教师,我也是父亲的学生。每天晚上,我与父亲在煤油灯下做着自己的事。父亲备课,改作业,我做作业。一旦我的作业做完后,父亲叫我帮他改作业。一来可以帮父亲的忙,二来可以巩固我所学的知识。很多时候,我都是强打精神。煤油灯的火苗忽闪忽闪的,父亲用手调整灯芯子,轻轻地拧着。调好了,灯光又稳稳地罩住了这个小小的世界。从窗子里望出去,邻家的窗口也亮着煤油灯,我知道,那家的孩子也在学习,那里也有个小小的世界。这时候,煤油灯又似乎特别柔和了,如同我自己轻盈的心境。
初中我在乡上读的。那时虽然安了电灯,但经常停电,也要用煤油灯。因此,学校每个住校生都自觉地准备了一盏煤油灯,以供停电之需。在停电时的晚自习,煤油灯闪烁在每间教室,从教室里泛出一点点红晕,红红的,很好看。读高中时,学校九点就熄了灯,这远远不能满足我读书的需要,我于是带了一盏煤油灯到寝室。我会点亮那盏煤油灯,看小人书,看哥哥给我的大专中文课程,我尤其喜欢读诗,读散文。就是在那时,我接触了文学,便也爱上了文学。记得父亲给了我一本他青年时代爱看的《毛泽东诗词集》,我在煤油灯下读了好几十遍,我便爱上了古典诗词,爱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,对他十分崇拜和敬仰。无疑,煤油灯下读书的经历,丰富了我的人生,为我后来走上文学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半夜看书入迷的时候,火烧眉毛属于正常,头发就更不用说了。有次,我把煤油灯放在床上看书,把被子点着了。从此,我只好半夜坐在地上看书。风从门缝吹进来,煤油灯开始晃动,于是,我靠着门板,把煤油灯架在凳子上看书。那个学习的姿态保持了好多年,盯着跳跃的火苗思索了很多年。
陪伴煤油灯最多,时间最长的是母亲。每每一觉醒来,看到煤油灯依然亮着,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母亲忙碌的身影。做棉鞋,织毛衣,一直纳呀,织呀,一生对儿女的情对儿女的爱都在密密麻麻的鞋底里,针脚里,在儿女们的生命里,在对儿女们的希望里。每天晚上,母亲除了做棉鞋,织毛衣,还要在煤油灯下拌猪食,喂猪,把猪儿喂得肥滚滚的。那时,卖猪是家里最大的收入。虽然父亲是教师,但由于缺劳力,又有我们三姊妹同时读书,家里经济并不好,除了父亲微薄的工资,母亲养副业挣钱,供我们生活和学习。父亲和母亲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,我们生活得很开心,很幸福。
现在的灯具新颖别致,或缤纷,或简洁,或耀眼,令人目不暇接。如今,告别煤油灯几十年了,但我心里一直忘不了那盏伴我走过童年少年的小煤油灯。它也曾点亮过我的人生,它那随风忽闪的亮点永远不会熄灭,永远闪烁在我的心里。
作者简介:
贾海,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龙蟠初中语文一级教师,内江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终身客座教授。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作协副主席。在各级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歌词30余万字。著有个人散文集《等待》《那片海》。曾获四川散文奖、第二届大巴山文艺推优工程优秀作品奖。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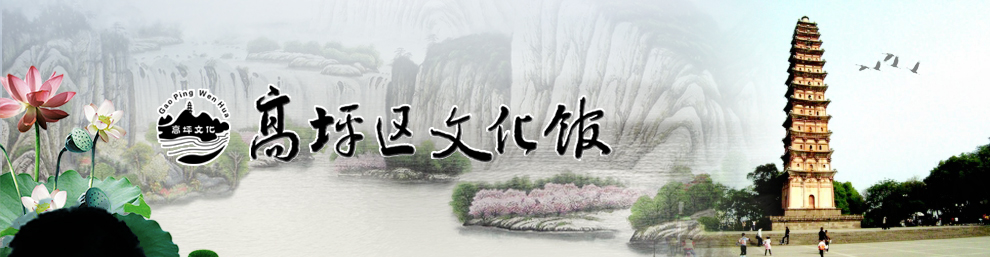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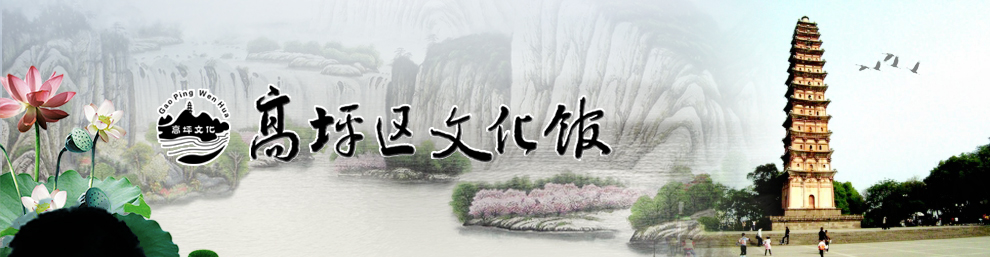
 川公网安备51130302000207号 本站访问量:4739520 蜀ICP备2023029787号-2
川公网安备51130302000207号 本站访问量:4739520 蜀ICP备2023029787号-2